“1976年9月12日,您先坐,我再倒杯水。”李敏轻声招呼,话音微颤。客厅里黑纱环绕的遗像让空气格外安静融通资产,王鹤滨点点头,抬手擦了擦镜框边角的灰尘,仿佛这样就能离那位故人更近一点。

从1949年秋天第一次见到毛主席算起,王鹤滨已整整二十七年没和李敏单独说过话。那年,他奉命护送李敏、李讷去报到,手续表格上“父亲”一栏让他犯难,带回中南海请示后,主席只摇头笑道:“学生是你送的,写你的名字。”一句话,既避嫌也护短,王鹤滨当场领会,笔下一落,两位“新女儿”便写在了档案里。
挂名父亲的结果出乎意料。李敏对这位“王叔叔”心生依赖,高中住院时更把情窦初开的烦恼递到他手心。那封折角的信纸今天仍留在王鹤滨的行医日记里:男孩字迹端正,句句朴实。王鹤滨揣摩少女的羞涩,提笔帮她回信,只叮嘱一句“慢慢了解”,没想到竟成了牵线之举。
1958年以后,王鹤滨调往军区总医院,再无机会直面主席。他常说自己“离灯塔太远”,却依旧把毛家姐妹的事挂在心上。1975年,偶遇李敏于北京协和医院门口,他脱口而出:“帮我捎封信给你父亲吧。”信里只是问候与保重,可他不了解,彼时李敏已因保密与治疗安排,极难见到父亲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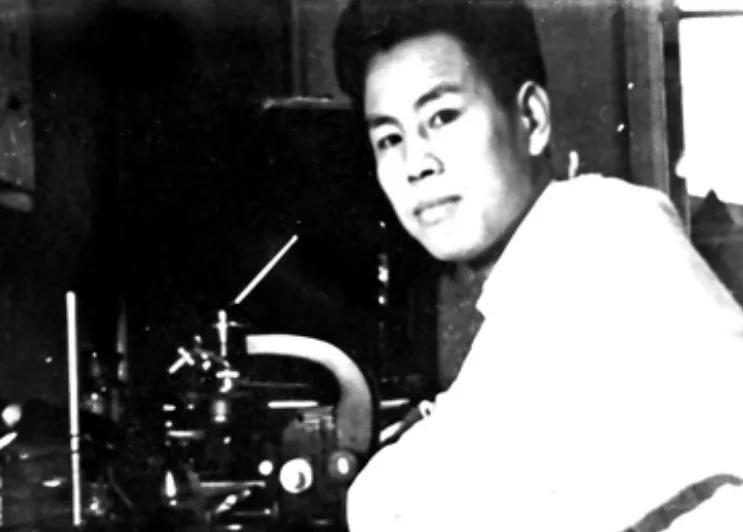
如今主席长眠,遗像中央,李敏挽着一位身着深灰中山装的男子走近。“王医生,这位是孔令华。”随即侧头对丈夫笑道:“咱俩能走到一起,多亏他。”话音落地,三人会心,却各怀思潮翻涌。
孔令华其实并不陌生。王鹤滨瞄了一眼对方融通资产,五官与当年信纸背后的想象重合:温和、有些书卷气,不善言辞却目光真诚。他伸手相握,对方微微鞠躬,短短几秒,旧事如电影般闪回;病房、床头柜、那封信、李敏半掩的笑意,一切都活了。

吊唁结束,三人落座。王鹤滨压低声音,仍难掩激动:“1975年的那封信,主席收到了吗?”李敏神情有歉:“爸病情反复,我实在琢磨不出办法,只好先瞒着您,信一直在我抽屉里。”说着取出一个牛皮信封,边角已微卷。王鹤滨握在手中,沉默良久,最终只是长叹:“我理解。”
不得不说,这段插曲让在场两位中年男人都生出复杂滋味。孔令华走南闯北多年,仍第一次知道妻子与岳父之间见面竟如此艰难。他轻轻拍拍李敏手背,对视片刻,便替她把尴尬接了过去:“当年要不是王医生提点,我恐怕连回信都收不到。”

客厅窗外,初秋阳光浅淡。李敏转身整理遗像下方的白菊,语气平稳却带一点感慨:“我和讷讷从小被嘱咐,不能仗着父亲身份去享便利。王叔那回把名字写上去,我们才真正明白‘普通学生’四个字的分量。”
王鹤滨听得认真。他曾在战地救护里见惯生死,也见过高级干部子女接受特殊待遇,而毛主席让两个女儿以普通身份入学的选择,令他佩服至今。他回忆道:“后来的教学主任还专门问我,你和孩子们什么关系。我说自己是送表的护士长,主任笑而不语,却再没追问。”

时间进入1960年代,国内局势起伏,王鹤滨忙于巡诊,几乎与李敏失联。他们再次通信,是1971年“九一三”后汛期支援,一封“注意安全”的纸条,行迹简单却暖意十足。李敏事后回忆,那是她收到的最及时的安慰。
环顾李敏家的书柜,《朝鲜战争医疗手记》被放在显眼位置,那是王鹤滨出版的小册子。孔令华拿下来翻阅两页,微笑道:“这本我在部队时读过,没想到作者本人比书写得更谦和。”王鹤滨摆手:“都是些救急的经验,谈不上大作。”简短客套,折射出那个年代同辈人特有的清正。
短暂停留后,王鹤滨起身告辞。临出门,他忽而想起一事,转回身语速放缓:“小孔,小李,若哪天你们有了孩子,别忘了带来看看我这位‘老丈人’。”李敏失笑:“那敢情好,届时还请您把名字再写一次?”气氛轻松了些,却没人再谈及沉重的别离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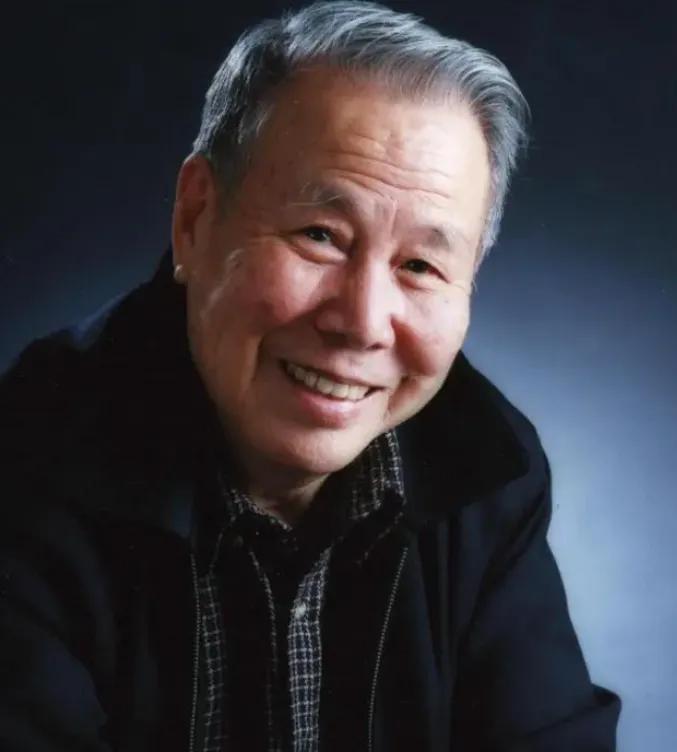
街道上梧桐叶摇摇坠坠,王鹤滨拎着那封未寄出的信,步子不快。偶尔路人投来好奇目光,他沉默前行,只在心里把那句未说出口的话默念了一遍:主席,学生给您来迟了。
融创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